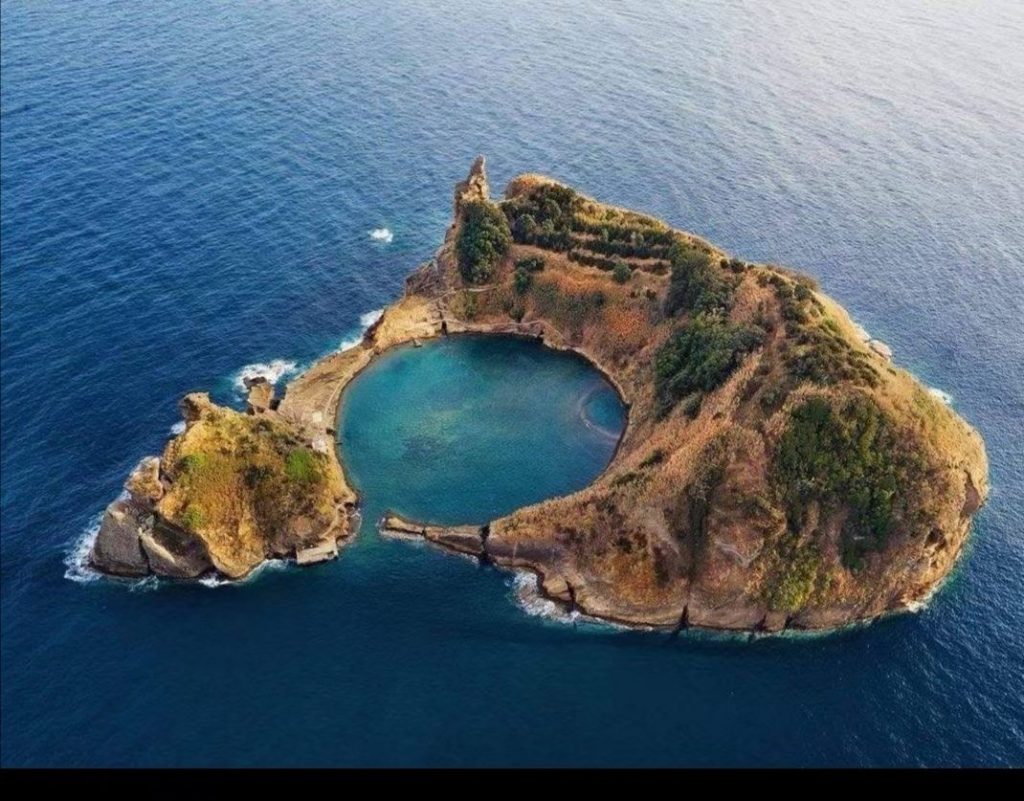《七十空性论》略释
先潘囊瓦尊者 著
堪布索达吉 译
梵音:新大撒哲嘎(日/阿)嘎那玛
藏音:东巴涅扽解波测雷额许瓦西夏瓦
汉意:七十空性论颂
敬礼曼殊室利童子!
(原译:敬礼曼殊室利智慧萨埵!)
生住灭有无 以及劣等胜
佛依世间说 非是依真实
生、住、灭、有、无,以及低劣、平等、超胜之类的这一切法,都是出有坏佛陀从世间名言的角度而言的,而不是从真如法性的角度而言的。
无我非无我 非故无可说
一切所说法 性空如涅槃
如果对方提出:难道人们津津乐道的诸如“我”等之类的法真的不存在吗?(如果真的不存在,)则因为“无我”的概念可得的缘故,所以我也就毋庸置疑地真实存在了。
无我以及非无我,也因为有我、我以及无我被否定了的缘故,所以无可诠说。为什么呢?因为一切所说之法,都如同涅槃,诸法的自性都为空性。
一切法自性 于诸因缘中
若总若各别 无故说为空
如果对方问道:像这样的(诸法自性为空)的说法,究竟是如同国王下达的圣旨一般,(以强权相威胁而必须服从,)还是因为通达“一切万法自性皆空”确有其理证呢?
一切诸法的自性,无论是在因缘、各个因缘的聚合[总]、分散的任一法[各别]上都不存在。既然如此,所以就只能说一切诸法的自性为空。
有故有不生 无故无不生
违故非有无 生无住灭无
另外,由于法已经存在,所以已有的法不可能从因法而生。因为我们都承许“有法正存在”的缘故;由于不存在的缘故,无有的法也不可能从因法而生;由于(二)法相违的缘故,有无二者兼具的法不可能生;同理,也由于(二)法相违的缘故,有无二者皆非的法也不可能生。
这样一来,因为生法不存在,住法与灭法也就不可能存在了。
已生则不生 未生亦不生
生时亦不生 即生未生故
如果对方提出:佛陀在经书中也说过,有为法具备生、住、灭三种法相。
并且,在正当产生之时也可以示现生法,因此,生法必定存在。
已经产生的某法,不可能是所生之法,因为已经产生过了的缘故;尚未产生的法,也不可能是所生之法,因为还没有产生的缘故;又因为在已生和未生之法以外,不存在其他的法,所以正在产生的法也不会是所生。
有果具果因 无果等非因
非有无相违 三世亦非理
另外,因为从因法的角度来说不应理的缘故,所以也不会有生:
首先,如果果法已经存在,则不需要因法,既然如此,具备果法的因法也就与非因法毫无二致了;其次,如果果法不存在,则因法也就不会有作用,没有作用的因法与非因法也是完全等同的;如果果法既非有也非无,则成了相违之法位于同体的法(,所以也不合理)。
还有,如果从三时的角度进行分析,因法也不合理。为什么呢?
因为,如果因法在前面,那么(所谓的因法)又是谁的因呢?如果因法在后面,则因为(果法)已经成立的缘故,又怎么会需要因法呢?如果因果位于同时,(那么请问,这种同时所生的因果,)究竟谁为谁因?谁是谁果呢?因此,从三时而言因法也不应理。
无一则无多 无多亦无一
以是一切法 缘起故无相
如果对方提出:因为数字是应理的,所以一切万法不应该是空性。既然存在一、二以及许多之类的数字,而(这些)数字却必须因诸法的存在才可能合理,因此,一切万法不应该是空性。
如果所谓的一不存在,则不可能存在多;反之,如果多不存在,则一也不应该存在。因此,自缘而起的诸法,是不会有相的。
缘起十二支 有苦即不生
于一心多心 是皆不应理
如果对方提出:佛经中曾广说过缘起能生苦果的道理,演说佛法的各大传教者,也宣说过一心以及多心。既然如此,诸法就不应该是空性。
(佛经所说的)由十二缘起[有支]所产生的苦果,其自性本为无生。因为因果不可能俱生,所以一心之说不合理;又因为前前支已经息灭,则不应该为后后支之因,所以多心之说也不合理。因此,(缘起之苦果)不会有生。
非常非无常 亦非我无我
净不净苦乐 是故无颠倒
我们还可以对无明[十二有支之第一支]之缘——颠倒[常、乐、我、净]进行观察:
因为互相观待的缘故,所以既不会存在常,也不会存在无常;同理,我与无我不会存在;净与不净不会存在;乐与痛苦也不会存在。因为这一切法都是互相观待的法,所以,四种颠倒就不可能存在。
从倒生无明 倒无则不有
以无无明故 行无余亦无
既然四颠倒不存在,那么由四颠倒而产生的无明也就不可能存在;既然无明不存在,则诸行也就不会产生。这样一来,其余的识等有支也就可以依此类推(,并从而得出不存在的结论)。
离行无无明 离无明无行
彼二互为因 是故无自性
另外,在诸行不存在的情况下,无明也不会产生;反之,在无明不存在的情况下,诸行也不会产生。因为互相为因而生的缘故,所以其二者的自性也无法成立。
自若无自性 云何能生他
以缘无性故 不能生于他
既然本身的自性都无法成立,又怎么可能产生他法呢?自身本体无法成立,尚且需要依靠他法而成立。但是,即使依靠他缘,也不应该产生[成立](,因为无有本体的缘故)。
父子不相即 彼二亦非离
亦复非同时 有支亦如是
因为父亲并不是儿子,儿子也并不是父亲,其二者既非互不观待,其二者也不是位于同时,所以父亲与儿子都不可成立。同样,十二缘起的产生也是如此。
梦境生苦乐 彼境亦非有
如是缘起法 所依缘亦无
还有,如同依靠梦境而产生的苦乐,以及苦乐二者的对境并不存在一样,如果是依靠某法而产生的,那么,这种缘起法,以及所依之缘都不可能存在。
若诸法无性 应无劣胜等
及种种差别 亦无从因生
如果对方提出:倘若诸法的自性都不存在,那么低劣、平等、超胜之法,以及形形色色的众生也就无法成立,还有,从因缘而生的观点也绝不可能成立。
有性非缘起 若非缘起法
无性云何成 实无实亦然
(原译:有性不依他,不依云何有?不成无自性,性应不可灭。)
如果诸法的自性成立,则不应该是缘起之法;如果不是缘起之法,无有自性又怎么成立呢?因此,诸法的有实与无实都不可成立。
无中云何有 自他性及无
故自性他性 性无性皆倒
(原译:自他性及灭,无中云何有?故自性他性,性无性皆倒。)
如果对方提出:因为不可能不依靠“自法、他法以及无实”之类的概念,所以诸法不应该是空性。
如果不存在自性,那么“自法、他法以及无实”又怎么可能成立呢?因此,“自法、他法以及无实[无性]”之说,完全是颠倒荒谬的。
若诸法皆空 应无生无灭
以于性空中 何灭复何生
如果对方提出:倘若一切万法都为空性,则既不可能有灭,也不可能有生。以本体而空的法,怎么可能有灭,又怎么可能有生呢?生灭二者都不可能成立。
有无非同时 无无则无有
(原译:生灭非同时,无灭则无生。)
一切万法绝对是空性。为什么呢?因为,诸法的有实与无实不可能位于同时,如果无实不存在,则无法观待无实的有实也不可能存在。
应常有有无 无无则无有
无有亦无无 不从自他生
是故有非有 无有则无无
(原译:应常有生灭。无生则无灭,无生时无灭。不从自他生,是故生非有,无生则无灭。)
如果(有实无实)位于同时,则有实无实二者就应当恒常存在。但是,如果没有无实,则不会有有实;反之,如果没有有实,也不存在无实。
诸法既不可能从自己而生,也不可能从他法而成。因此,如果有实不存在,则无实也就无法存在;既然无实也不存在,又有什么法会存在呢?(任何法都不可能存在!)
有有性应常 无者定成断
有性堕二失 是故不应许
(原译:有生性应常;无者定成断。有生堕二失,是故不应许。)
如果有实存在,则成为了恒常;如果承许无实,则必定会有断灭的过失。如果承许诸法实有,就会堕犯以上两种过失之一。因此,我们不应该承许诸法为实有。
相续故无过 法与因已灭
此如前不成 复有断灭过
如果对方提出:因为有相续的缘故,所以没有常断之过。因法在给予果法以因法后,因法的本性就已经毁灭。(因为存在相续,所以不会断灭;又因为因法会毁灭,所以也不会堕入常见。)
正如前面所说的,有实与无实二者不可能处于同时一样,(你们所承许的这种因果,)同样不可成立,仍然有(堕入常边与)断灭之过。
佛说涅槃道 见生灭非空
此二互违故 所见为颠倒
如果对方提出:由于现见生灭,佛陀才宣说了涅槃之道。因此,诸法不应该为空性。
因为生灭二者是互相抵触的法相,所以,“现见生灭”之说完全是颠倒错乱的。
若无有生灭 何灭名涅槃
自性无生灭 此岂非涅槃
如果对方提出:如果没有生灭,又会因什么法的寂灭而获得涅槃呢?
如果自性既无生也无灭,难道还不是涅槃吗?
若灭应成断 异此则成常
有实与无实 涅槃皆不许
(原译:若灭应成断;异此则成常。涅槃非有无,故无生与灭。)
还有,如果承许以寂灭而获得涅槃,则成了断见;如果承许涅槃另外存在而不会有毁灭,则又堕入了常见。因此,无论有实还是无实,对于涅槃而言都不合理。
灭若常住者 离法亦应有
离法此非有 离无法亦无
如果对方提出:灭法是存在的,并且恒常安住。
如果有某个灭法会恒常安住,则应该存在于诸法之外,但这是不应理的。因为,如果离开了有实法,则不会有灭法;也正因为离开了有实法,所以无实法也不可能存在。
能相与所相 相待非自成
亦非展转成 未成不能成
为什么呢?因为,诸法的事相[能相],是观待其自身之外的法相[所相]而成立的;反之,(法相)也是依靠事相而成立,不可能依凭自己而成立。事相法相二者,也不可能彼此依靠展转而成。因为尚未成立之法不可能成为未成之法的能成[能立]。
因果受受者 能见所见等
一切法准此 皆当如是说
因此,包括因法与果法、受法与受者、能见与所见等等一切万法,都可以参照以上推导进行宣说。
不住相待故 乱故无体故
无性故三时 非有唯分别
如果对方提出:因为研究时间的学者认为三时存在,所以时间应该存在。
因为(三时)不可停驻,因为(三时)互相观待而成,因为(三时)会相互错乱,因为时间的本体不可成立,又因为安立时间的基础[性]不存在的缘故,所以三时也就不可能存在。所谓三时之说,完全是分别妄念。
由无生住灭 三种有为相
是故为无为 一切皆非有
如果对方提出:佛经中说,一切有为法都具备生、(住、灭)等三种法相,与其相违的法,即是无为法。因此,有为法与无为法应该存在。
如果对生、住、灭这三种有为法法相进行观察,则可知其无有丝毫自性。因此,有为法既不应该存在,无为法也不应该有一鳞半爪的存在。
还有,如果承许有为法存在,则因为经不起审慎观察的缘故,所以(有为法)的自性不可能存在。
灭未灭不灭 已住则不住
未住亦不住 生未生不生
如果这样承许(有为法存在,那么请问),在毁灭之时,究竟是未灭的法毁灭,还是已灭的法毁灭呢?(但这两种说法都不合理。因为,)首先,未灭的法不可能毁灭,因为尚未毁灭的缘故;其次,已灭的法也不可能毁灭,因为已经毁灭的缘故。同理,已住的法不可能驻留,因为已经驻留的缘故;未住的法也不可能驻留,因为尚未驻留的缘故;已生的法不可能产生,因为已经产生的缘故,未生的法也不可能产生,因为尚未产生的缘故。
有为与无为 非多亦非一
非有无二俱 此摄一切相
如果对有为法与无为法进行详细观察,则既不可能是多,也不可能是一;既不可能是有,也不可能是无,还不可能是亦有亦无。而以上情形,已经涵摄了(有为法与无为法)森罗万象的一切法相。(因此,有为法与无为法绝不可能存在!)
世尊说业住 复说业及果
有情受自业 诸业不失亡
如果对方提出:众生导师世尊也说过业之存在[住]、业之本体、业之果法,有情承受自(作)之业(果),诸业无有失耗的道理。因此,业与业果是存在的。
已说无自性 故业无生灭
由我执造业 执从分别起
佛经中已经说过:“诸业无有自性。”所以无生之业也不会失坏[灭]。诸业是从我执而生,而产生诸业的我执又是从分别妄念而生。
业若有自性 所感身应常
应无苦异熟 故业应成我
如果诸业存在自性,则从彼业所感的身体就应当成为恒常,身体也就不会成为痛苦的异熟果(1)。又因为是常有的缘故,我也就随之而成立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无常即是痛苦,而痛苦即成无我。(反之,如果是常有,即可因此而成立我。)
由此可知,正因为业无有自性,所以无生;又因为无生,所以不会失耗。
业缘生非有 非缘亦无有
诸行如幻事 阳焰寻香城
业不可能从缘而生,也没有丝毫从非缘而生的可能。为什么呢?因为,诸行如同幻觉、如同寻香城、如同阳焰,所以业无有自性。
业以惑为因 行体为惑业
身以业为因 此三皆性空
还有,诸业是以烦恼为因,烦恼与诸行为业的本体(2),而身体又是诸业的果法。所以,其三者[业之因法——烦恼,业之本体——烦恼与诸行,业之果法——身体]的本体都为空性。
无业无作者 无二故无果
无果无受者 是故皆远离
因为果法无有自性,所以业也不可能存在;既然业不存在,则作业者也不会存在;因为业与作者二法都不存在,其果法也就不可能存在;既然果法不存在,则(果法的)承受者也不可能存在。因此,诸法都是远离自性的。
若善知业空 见真不造业
若无所造业 业所生非有
如果能真实通达诸业为空的道理,彼人则因现见真如法性的缘故,而不会再造业;如果不会造业,则自业所生之法也就不会存在了。
如佛薄伽梵 神通示化身
其所现化身 复现余变化
如果对方提出:这一切是绝对不存在,还是有稍许存在呢?
可以存在。怎么存在呢?
如同佛陀世尊以神通而幻化出化身,此(幻化出的)化身又幻化出其余化身。
佛所化且空 何况化所化
一切唯分别 彼二可名有
如来所幻化(的化身)自性尚且为空性,又何况该化身所幻化的(其余)化身呢?
业与所作等等二者也是徒有其名,这一切都仅仅是分别而已。
作者如化身 业同化所化
一切自性空 唯以分别有
同理,作业者如同(佛陀所幻化出的)化身,业又如同化身所化出的其余化身。
因为以自性而空,所以任何点滴的存在都只不过为分别而已。
若业有自性 无涅槃作者
无则业所感 爱非爱果无
如果业的自性存在,则因为自性成立的缘故,所以不可能存在涅槃以及自作者而生之业,(因为不存在自作者而生之业,所以作者也就无法存在了)(3);反之,如果业的自性不存在,则从业而生的果法——贪爱与厌憎也不可能存在。
说有或说无 或说亦有无
诸佛密意说 此难可通达
如果对方提出:经中曾不吝笔墨地宣说过:“诸业存在”的道理,(既然如此,业又)怎么可能不存在呢?
所谓“存在”之说,只不过是假立而有的;所谓“不存在”之说,也是假立而有的;而所谓“亦有亦无”之说,还是假立而有的。
佛陀以密意而宣说的这些道理,是非常难以通达领会的。
色从大种生 则从非真生
非从自性生 彼无非他生
如果对方提出:色法是由大种而产生[大种所造]的,(所以应该存在,)既然色法存在,其余非色诸法也应当存在。
如果色法是从大种而产生的,则应该是从非真实或者非自性中产生了色法。
既然色法不是从自性而生,又因为他法不存在的缘故,所以也不可能从他法而生。
诸大种也不可能存在。因为,如果承许大种从法相而生,则法相成立于大种之前的前提也无法立足。
如果法相不成立,则事相,也即大种也无法成立。
一中非有四 四中亦无一
依无四大种 其色云何有
在一种色法之类的法中,不可能存在四大种;而在四大种中,也不可能存在一种色法。既然如此,以(原本无有的)四大种为因而成立的色法,又怎么可能存在呢?
最不可取故 由因因亦无
从因缘生故 因无有非理
(原译:最不可取故,由因因亦无,从因缘生故,有无因非理。)
还有,因为色法是极其不可执取的,所以不可能存在自性。
如果认为以执取色法所存在的心为因[推断],并从中可以推知(色法)。但你们所声称的这种作为因的心,也是不存在的。
因为是从因缘而生的缘故,所以这种所谓的因不可能存在,这样一来,色法的存在也就无法以理服人了。
若谓能取色 则无取自体
缘生心无故 云何能取色
如果承许以识可以执取色法,则成了自体能取自体。然而,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,也就是说,以识根本不可能执取色法。这样一来,以自性而空的识[缘生心]为缘所产生的法也就不可能存在。既然所生之法不成立,(以识)又怎么能执取无色呢?(绝不可能!)
以刹那生识 不取刹那色
云何能通达 过去未来色
(原译:能刹那生心,不取刹那色。云何能通达,过去未来色?)
如果对方提出:佛经中曾浓墨重彩地宣说过“色法之过去与未来可执”的道理,因此,执取色法应该存在。
以刹那而生的识,是不可能执取这种刹那而生的所谓色法的,既然如此,这种识又怎能通达过去以及未来之色呢?因为不存在的缘故,所以不应该通达。
显色与形色 异性终非有
不应取彼异 许同是色故
还有,虽然我们承许显色与形色,但执取色法之说还是不应理。为什么呢?因为,显色与形色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异体,所以不应该存在执取它们为异体的情形。
如果其二者为异体,则因为显色与形色同为色法的缘故,所以不应理。
眼识非在眼 非色非中间
彼依眼及色 偏计即颠倒
眼识既不存在于眼根之上,也不存在于色法之上,而在眼根与色法的中间,也不可能存在眼识,因此,依靠色法与眼根所产生的通晓(诸法的眼识),纯粹是一种颠倒之念。
若眼不自见 云何能见色
故眼色无我 余处亦同尔
如果对方提出:眼根等诸处是存在的,因为其行境所见等等存在的缘故。
如果眼根不能见自性,又怎么能见到色法呢?因此,眼根与色法二者是不存在自性的。同理,耳根与声音等其余诸处也同样不存在自性。
眼由自性空 复由他性空
色亦如是空 余处空亦尔
眼根既以自性而空,也以他性而空;色法也同样以自性与他性而空。耳根与声音等其余诸处也同样为空性。
另外,因为(诸处)是缘起之法的缘故,所以也应该是空性:
因为色法的产生是以因缘而成立的,所以色法应当是缘起之法。而任何以缘起而成立的法,其自性都不可成立。所以,色法的自性应当是空性。
而所谓的他性,也应当是空性。因为,(作为他性的)眼根与眼识也一样(为空性)。(我们都知道,)包含眼识在内的眼根即为有境,而色法即为对境,对境并不是有境。因此,(色法的)他性也应该是空性。
另一种说法为:因为(眼)识是里面的法,而色法却是所作以及外面的法,因为不是里面的法,所以他性应该是空性。
为什么呢?因为眼识是依靠(他法)而产生的。
如何依靠(他法)而产生呢?眼识是依靠所知等等而成立的。凡是依靠(他法)而成立的法,就不会有自性,所以眼识无有自性。因此,所谓“眼识可以执取细微色法等等”的说法,是毫无道理的。
所谓“色亦如是”的说法,也就是说(色法)也与其[眼根或者眼识]相同。就像眼根是以自性以及他性而空一样,色法也是以自性以及他性而空。
为什么色法是以自性以及他性而空呢?正如前面所说:“一切自性空,唯以分别有。”如果审慎观察,一切法都不存在,即是“一切诸法皆无自性”的另一种说法;所谓“空”,即是“不可得”的另一种说法;
因为眼根是缘起之法的缘故,所以是空性,也即为:眼根是缘起而成之法。而任何缘起而成之法,其自性都不可成立,因此,眼根的自性为空性。但是,如果承许他性存在,也不合理。
为什么呢?因为,任何无有自性之法,其所谓的他法又怎么能在何处存在呢?这样的所谓他法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因此,他性也必然是空性。
还有一种说法为:所谓“他性亦为空”中的“他”,即表示(眼)识,即为“眼根以眼识亦空”的另一种说法。
为什么呢?因为,在眼根上面是不存在眼识的,既然没有眼识,则“具有眼识”的自性就不应该成立,所以,他性也就成为了空性。
若触俱一起 则余者皆空
空不依不空 不空不依空
如果一个“处”与“触”共同在一起的时候,其他的法也就成了空性。空性不依赖于不空,不空也不依赖于空性。
三非有自性 不住无和合
则无彼性触 是故受亦无
因为自性不住以及不存在[非有],所以三者的和合也不可能存在。既然和合不存在,则不存在它们之间的“触”,此时,由触而生的受也就不可能存在了。
彼止内外处 而有心识生
是故识非有 如幻如焰空
依靠内外各处,从而产生了心识,因为心识是依缘而生之法,所以如同阳焰以及幻觉一般为空性。
由依所识生 是故识非有
识所识无故 亦无有识者
而所谓的心识,又是依靠所识而产生的,但所识的自性却并不存在,(所以心识也不可能存在。)(4)既然所识与心识都不存在,识者也就不可能存在了。
一切无常者 非常无有常
常无常依性 其性岂能有
如果对方提出:佛经云:“诸法无常。”既然宣说了诸法无常,其实也就是在宣说诸法不空。(因此,诸法不可能为空性。)
因为一切万法皆为无常,也就是“非常”或者“不存在常有”的意思。如果诸法[性]存在,所谓的常与无常就可以成立。但是,诸法[性]又怎么会存在呢?不可能存在。
爱非爱颠倒 缘生贪嗔痴
是故贪嗔痴 非由自性有
如果对方提出:因为佛经中曾广为宣说的缘故,所以贪嗔痴诸法应当存在。
因为是由贪爱之缘、嗔恨之缘以及颠倒之缘,才产生了贪爱、嗔恨以及愚痴的缘故,所以贪嗔痴不可能以自性而存在。
于彼起贪欲 嗔恚或愚痴
皆由分别生 分别非实有
(对于同一个对境,)有的人贪爱其境,有的人嗔恨其境,而有的人又对其蒙昧无知,由此可见,这一切都是由分别念而产生的。而分别念本身,又并不是真实实有的。
所分别无故 岂有能分别
以是缘生故 能所别皆空
为什么不是真实实有的呢?因为,任何所分别之法都不可能存在。既然没有所分别,又怎么会存在能分别呢?因为所分别与能分别都是从缘而生的缘故,所以其自性都为空性。
四倒生无明 见真则非有
此无故行无 余支亦如是
如果能证达真如法性,则不会再有从四颠倒而产生的无明;如果没有无明,则不会产生诸行……依此类推,其余识等有支也就同样不可能存在了。
依彼有性生 彼无此不有
有无即有为 无为乃涅槃
(原译:依彼有性生,彼无此不有。有性及无性,为无为涅槃。)
某法以及依靠某法而产生的有实法,不但彼法不存在,从不存在的彼法而生的此法也不会存在。
有实法与无实法二者,即为有为法;而无为法,也就是涅槃。
诸法因缘生 分别为真实
佛说即无明 发生十二支
将从因缘而生的诸法,分别执著为真如法性。佛陀就将此作法,称之为“无明”。从无明当中,就产生了十二缘起有支。
见真知法空 则不生无明
此即无明灭 故灭十二支
如果能证悟诸法自性为空,则因为现见真如的缘故,所以就不会生起蒙昧无明,这就是无明的毁灭;(因为无明已经毁灭的缘故,)则从已经毁灭的无明中所产生的所有十二有支也一并毁灭。
行如寻香城 幻发及阳焰
水泡水沫幻 梦境旋火轮
(原译:行如寻香城,幻事及阳焰,水泡与水沫,梦境旋火轮。)
为什么呢?如果详细观察就可以了知,诸行如同寻香城、如同幻觉、如同阳焰、如同(具眼翳者所见之)毛发,还如同水泡、水沫、幻术、梦境以及旋火轮等等,因此,其自性必然为空性。如果能善加了知(这一切),则不会产生无明。
无少自性法 亦非无有法
以从因缘起 法无法皆空
(此偈颂在藏文原版中缺漏。现依据龙树菩萨自释略作解释:如果仔细抉择,则既不可能存在少许具有自性的法,也不可能存在少许无有自性的法。因为有自性的法与无自性的法,都是从因缘而生的缘故,所以全都是空性。)
以此一切法 皆是自性空
故佛说诸法 皆从因缘起
因为一切诸法都以自性而空,所以无等善逝佛陀殷重地告诫世人:只有自缘而生、本体为空,并且寂灭一切有无戏论,才是诸法的实相。
胜义唯如是 然佛薄伽梵
依世间名言 施设一切法
在胜义中,一切缘起诸法都只可能是自性为空、无有戏论。但薄伽梵世尊针对世间人,依靠世俗名言,假立了纷纭繁杂的一切诸法。
不坏世间法 真实无可说
不解佛所说 而怖无分别
既不破坏从世间角度所宣说的诸法,而于真实性中却未曾宣说过任何法。因为不能解悟如来所宣说的这些道理,彼等愚夫就会对(如来)所说的这些无有污垢、不可言说、无有分别、无有法相的境界,生起恐怖之心。
依彼有此生 世间不可坏
缘起即无性 宁有理唯尔
虽然不破坏“依靠彼法而产生此法”的世间所成之理,但是,凡是依缘而生之法,其自性都不可能存在。而所谓不存在的自性,“又怎么可能存在呢?”真理必定是这样!
于具信求真 以理类推者
宣说无依法 离有无寂灭
(原译:正信求真实,于此无依法,以正理随求,离有无寂灭。)
对于具有正信,精勤寻求真实之义,并且于此所说能以正理类推的人们,(佛陀)又宣说了无所依之法,(以便其)能舍离有性无性二者,从而获得寂灭。(5)
了知此缘起 遮遣恶见网
断除贪嗔痴 趋无染涅槃
用这些(诸法)仅为缘起的道理,就能够遮遣一切恶见之网,因为这种人能够断除贪嗔痴的缘故,所以能不染诸垢而获得涅槃。
《七十空性论》,由圣者阿闍黎龙树菩萨圆满撰著完毕,并由译师旬呢却[童胜]、念达马扎[盛称]以及库•尊珠雍中(6)所译之词义善录而成。
依照前译派译师意西得[智军]等所译之(龙猛菩萨)自释本所作之此释文,是由前辈诸大菩萨译师之敬随者——贫僧先潘囊瓦恭书而成。愿吉祥!
重校于2007年12月11日
(1)此处与法尊法师所译的龙树菩萨《自释》说法不同,《自释》译为“彼业应无苦异熟果”,望斟酌。
(2)此处与法尊法师所译的龙树菩萨《自释》说法不同, 《自释》译为“诸行从业及烦恼为因而生”,望斟酌。
(3)此处藏文原文,与法尊法师所译的龙树菩萨《自释》说法不同,因《自释》观点比较容易理解,故未改偈颂,并将其注释内容加入()内,望斟酌。
(4)此处藏文原文,与法尊法师所译的龙树菩萨《自释》说法不同,因《自释》观点有一定道理,故未改偈颂,并将其注释内容加入()内,望斟酌。
(5)此处与法尊法师所译的龙树菩萨《自释》说法不同,《自释》中为“若成就正信勤求真实,于此所说都无所依之法,能以正理随求、随欲者,则能远离有性、无性而得寂灭。”望斟酌。
(6)库•尊珠雍中:阿底峡尊者三大主要弟子之一。

回向偈
文殊师利勇猛智, 普贤慧行亦复然,
我今回向诸善根, 随彼一切常修学。
三世诸佛所称叹, 如是最胜诸大愿,
我今回向诸善根, 为得普贤殊胜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