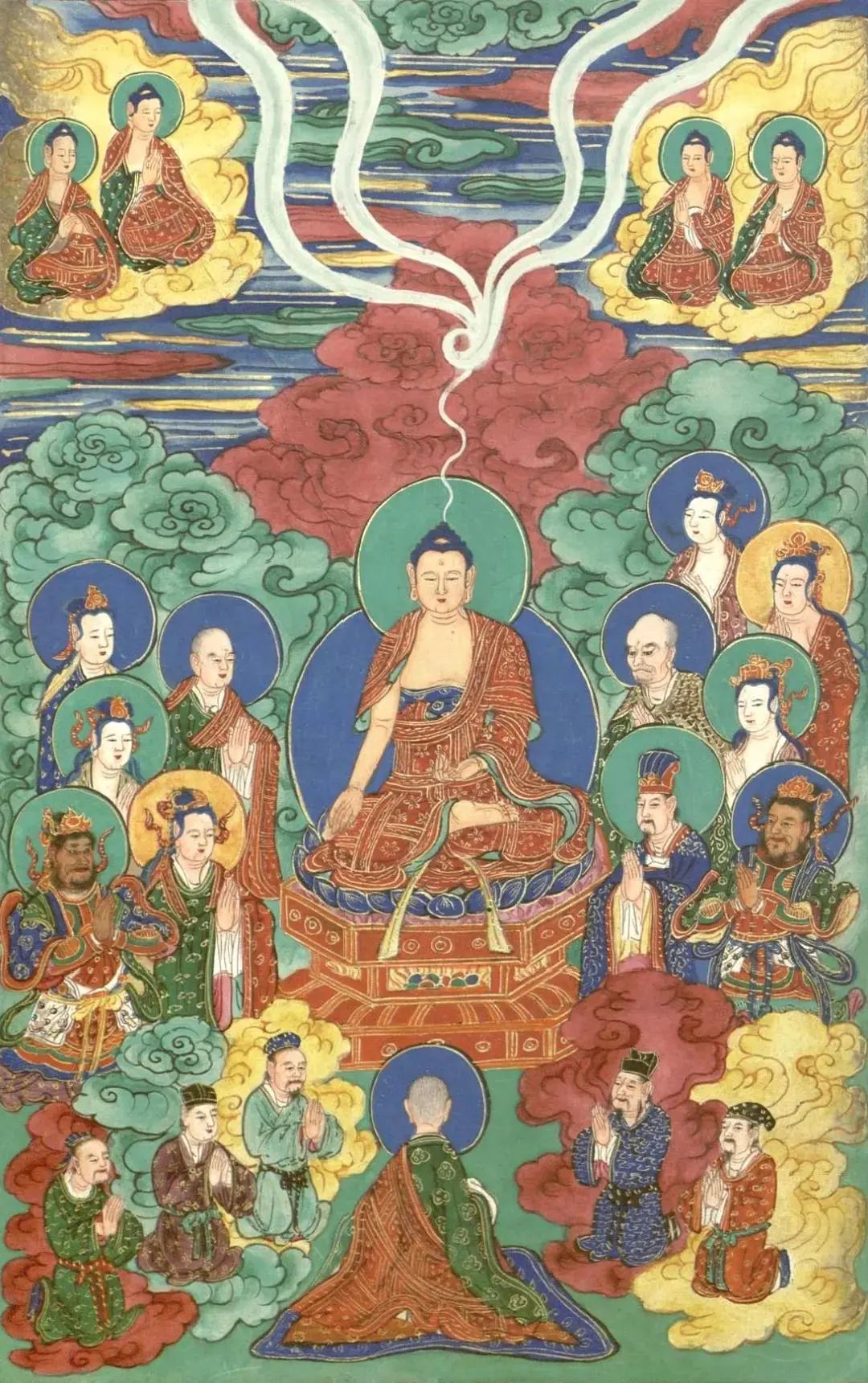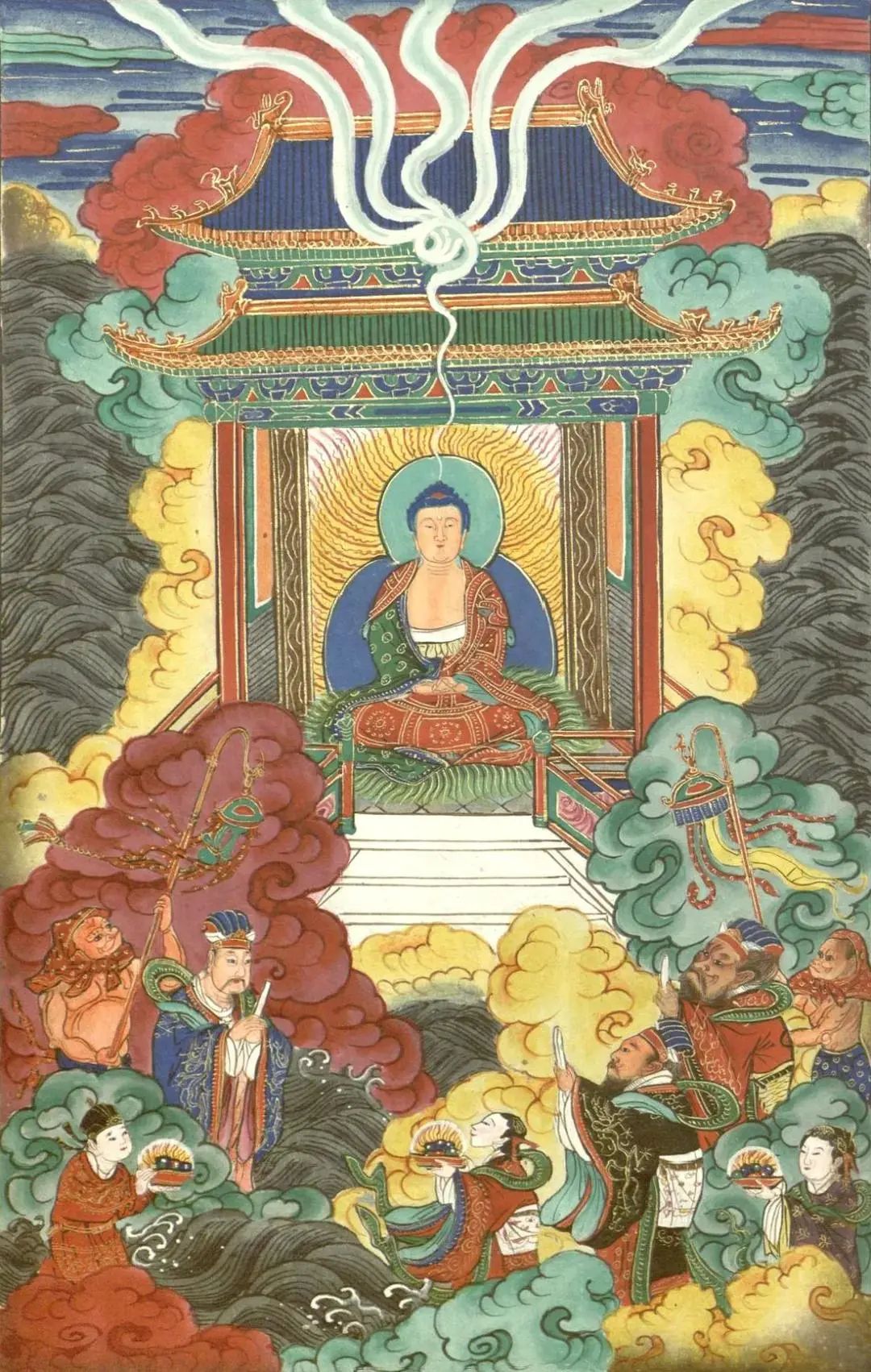《达摩大师血脉论》
— 渝州华严寺沙门释宗镜 校刻
三界兴起,同归一心,前佛后佛,以心传心,不立文字。问曰:“若不立文字,以何为心?”答曰:“汝问吾,即是汝心;吾答汝,即是吾心。吾若无心,因何解答汝?汝若无心,因何解问吾?问吾,即是汝心;从无始旷大劫以来,乃至施为运动,一切时中,一切处所,皆是汝本心,皆是汝本佛。即心是佛,亦复如是。除此心外,终无别佛可得;离此心外,觅菩提涅槃,无有是处。”
自性真实,非因非果。法即是心义,自心是菩提,自心是涅槃。若言:“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”无有是处。佛及菩提皆在何处?譬如有人以手捉虚空得否?虚空但有名,亦无相貌;取不得、舍不得,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觅佛,终不得也。佛是自心作得,因何离此心外觅佛?前佛后佛只言其心,心即是佛,佛即是心;心外无佛,佛外无心。若言:“心外有佛”佛在何处?心外既无佛,何起佛见?递相诳惑,不能了本心,被它无情物摄,无自由分。若也不信,自诳无益。
佛无过患,众生颠倒,不觉不知自心是佛;若知自心是佛,不应心外觅佛。佛不度佛,将心觅佛,而不识佛。但是外觅佛者,尽是不识自心是佛。亦不得将佛礼佛,不得将心念佛。佛不诵经、佛不持戒、佛不犯戒;佛无持犯,亦不造善恶。若欲觅佛,须是见性,见性即是佛。若不见性,念佛、诵经、持斋、持戒亦无益处。念佛得因果,诵经得聪明,持戒得生天,布施得福报,觅佛终不得也。
若自己不明了,须参善知识,了却生死根本。若不见性,即不名善知识。若不如此,纵说得十二部经,亦不免生死轮回,三界受苦,无有出期。昔有善星比丘,诵得十二部经,犹自不免轮回,缘为不见性。善星既如此,今时人讲得三、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,愚人也。若不识得自心,诵得闲文书,都无用处。
若要觅佛,直须见性。性即是佛,佛即是自在人,无事无作人。若不见性,终日茫茫,向外驰求觅佛,元来不得。虽无一物可得,若求会,亦须参善知识,切须苦求,令心会解。生死事大,不得空过,自诳无益。纵有珍宝如山,眷属如恒河沙,开眼即见,合眼还见么?故知有为之法,如梦幻等。若不急寻师,空过一生。然则佛性自有,若不因师,终不明了。不因师悟者,万中希有。若自己以缘会合,得圣人意,即不用参善知识。此即是生而知之,胜学也。若未悟解,须勤苦参学,因教方得悟。若自明了,不学亦得。不同迷人,不能分别皂白,妄言宣佛敕,谤佛妄法。如斯等类,说法如雨,尽是魔说,即非佛说。师是魔王,弟子是魔民,迷人任它指挥,不觉堕生死海。但是不见性人,妄称是佛;此等众生,是大罪人,诳它一切众生,令入魔界。若不见性,说得十二部经教,尽是魔说;魔家眷属,不是佛家弟子。既不辨皂白,凭何免生死?
若见性即是佛,不见性即是众生。若离众生性,别有佛性可得者,佛今在何处?众生性即是佛性也。性外无佛,佛即是性;除此性外,无佛可得,佛外无性可得。
问曰:“若不见性,念佛、诵经、布施、持戒、精进,广兴福利,得成佛否?”答曰:“不得。”又问:“因何不得?”答曰:“有少法可得,是有为法,是因果、是受报、是轮回法,不免生死,何时得成佛道?成佛须是见性。若不见性,因果等语,是外道法。若是佛,不习外道法。佛是无业人,无因果,但有少法可得,尽是谤佛,凭何得成?但有住著一心、一能、一解、一见,佛都不许。佛无持犯,心性本空,亦非垢净。诸法无修无证,无因无果。佛不持戒,佛不修善,佛不造恶,佛不精进,佛不懈怠,佛是无作人。但有住著心见佛,即不许也。佛不是佛,莫作佛解。若不见此义,一切时中,一切处处,皆是不了本心。若不见性,一切时中,拟作无作想,是大罪人,是痴人,落无记空中;昏昏如醉人,不辨好恶。若拟修无作法,先须见性,然后息缘虑。若不见性,得成佛道,无有是处。有人拨无因果。炽然作恶业,妄言本空,作恶无过;如此之人,堕无间黑暗地狱,永无出期。若是智人,不应作如是见解。”
问曰:“既若施为运动,一切时中,皆是本心;色身无常之时,云何不见本心?”答曰:“本心常现前,汝自不见。”
问曰:“心既见在,何故不见?”师云:“汝曾作梦否?”答:“曾作梦。”问曰:“汝作梦之时,是汝本身否?”答:“是本身。”又问:“汝言语、施为、运动,与汝别不别?”答曰:“不别。”师云:“既若不别,即此身是汝本法身;即此法身是汝本心。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,与如今不别;未曾有生死,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、不垢不净、不好不恶、不来不去;亦无是非,亦无男女相,亦无僧俗老少,无圣无凡;亦无佛,亦无众生,亦无修证,亦无因果,亦无筋力,亦无相貌;犹如虚空,取不得、舍不得,山河石壁,不能为碍;出没往来,自在神通;透五蕴山,渡生死河;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。此心微妙难见,此心不同色心,此心是人皆欲得见。于此光明中,运手动足者,如恒河沙,及于问著,总道不得,犹如木人相似,总是自己受用,因何不识?”
佛言:“一切众生,尽是迷人,因此作业,堕生死河,欲出还没,只为不见性。”众生若不迷,因何问著其中事,无有一人得会者,自家运手动足,因何不识?故知圣人语不错,迷人自不会晓。故知此难明,惟佛一人,能会此法;余人、天及众生等,尽不明了。若智慧明了此心,方名法性,亦名解脱。生死不拘,一切法拘它不得,是名大自在王如来;亦名不思议,亦名圣体,亦名长生不死,亦名大仙。名虽不同,体即是一。
圣人种种分别,皆不离自心。心量广大,应用无穷,应眼见色,应耳闻声,应鼻嗅香,应舌知味,乃至施为运动,皆是自心。一切时中,但有语言,即是自心。故云:“如来色无尽,智慧亦复然。”色无尽是自心,心识善能分别一切,乃至施为运用,皆是智慧。心无形相,智慧亦无尽。故云:“如来色无尽,智慧亦复然。”四大色身,即是烦恼,色身即有生灭,法身常住而无所住,如来法身常不变异。
故经云:“众生应知:佛性本自有之。”迦叶只是悟得本性,本性即是心,心即是性,即此同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传此心,除此心外,无佛可得。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,向外驰求,终日忙忙;念佛礼佛,佛在何处?不应作如是等见,但识自心,心外更无别佛。
经云:“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。”又云:“所在之处,即为有佛。”自心是佛,不应将佛礼佛;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,忽尔见前,亦切不用礼敬。我心空寂,本无如是相貌,若取相即是魔,尽落邪道。若是幻从心起,即不用礼。礼者不知,知者不礼,礼被魔摄。恐学人不知,故作是辨。诸佛如来本性体上,都无如是相貌,切须在意。但有异境界,切不用采括,亦莫生怕怖,不要疑惑,我心本来清净,何处有如许相貌?乃至天、龙、夜叉、鬼神、帝释、梵王等相,亦不用心生敬重,亦莫怕惧;我心本来空寂,一切相貌皆是妄相,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见、法见,及佛菩萨等相貌,而生敬重,自堕众生位中。若欲直会,但莫取一切相即得,更无别语。故经云:“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。”都无定实,幻无定相,是无常法。但不取相,合它圣意。故经云:“离一切相,即名诸佛。”
问曰:“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?”答曰:“天魔、波旬、阿修罗示见神通,皆作得菩萨相貌。种种变化,皆是外道,总不是佛。佛是自心,莫错礼拜。”
佛是西国语,此土云觉性。觉者灵觉,应机接物,扬眉瞬目,运手动足,皆是自己灵觉之性。性即是心,心即是佛,佛即是道,道即是禅。禅之一字,非凡圣所测。直见本性,名之为禅。若不见本性,即非禅也。假使说得千经万论,若不见本性,只是凡夫,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,不可话会,典教凭何所及?但见本性,一字不识亦得。见性即是佛,圣体本来清净,无有杂秽。所有言说,皆是圣人从心起用。用体本来空,名言尚不及,十二部经凭何得及?道本圆成,不用修证。道非声色,微妙难见。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不可向人说也。唯有如来能知,余人天等类,都不觉知。凡夫智不及,所以有执相。不了自心本来空寂,妄执相及一切法,即堕外道。若知诸法从心生,不应有执,执即不知。若见本性,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。千经万论只是明心,言下契会,教将何用?至理绝言;教是语词,实不是道。道本无言,言说是妄。
若夜梦见楼阁、宫殿,象马之属,及树木、丛林、池亭如是等相,不得起一念乐著,尽是托生之处,切须在意。临终之时,不得取相,即得除障。疑心瞥起,即被魔摄。法身本来清净无受,只缘迷故,不觉不知,因兹故妄受报。所以有乐著,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,即不染习。
若从圣入凡,示现种种杂类等,自为众生,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,一切业拘他不得。圣成久矣,有大威德,一切品类业,被他圣人转,天堂、地狱无奈他何。凡夫神识昏昧,不同圣人内外明彻。若有疑即不作,作即流浪生死,后悔无相救处。贫穷困苦,皆从妄想生。若了是心,递相劝勉,但无作而作,即入如来知见。
初发心人,神识总不定;若梦中频见异境,辄不用疑,皆是自心起故,不从外来。梦若见光明出现,过于日轮,即余习顿尽,法界性见。若有此事,即是成道之因。唯自知,不可向人说。或静园林中,行住坐卧,眼见光明,或大或小,莫与人说,亦不得取,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静暗中,行住坐卧,眼见光明,与昼无异,不得怪,并是自心欲明显。或夜梦中,见星月分明,亦自心诸缘欲息,亦不得向人说。梦若昏昏,犹如阴暗中行,亦是自心烦恼障重,亦可自知。
若见本性,不用读经、念佛,广学多知无益,神识转昏。设教只为标心;若识心,何用看教?若从凡入圣,即须息业养神,随分过日。若多嗔恚,令性转与道相违,自赚无益。圣人于生死中,自在出没,隐显不定,一切业拘他不得。圣人破邪魔,一切众生但见本性,余习顿灭。神识不昧,须是直下便会,只在如今。欲真会道,莫执一切法;息业养神,余习亦尽;自然明白,不假用功。外道不会佛意,用功最多;违背圣意,终日驱驱念佛、转经,昏于神性,不免轮回。佛是闲人,何用驱驱广求名利,后时何用?但不见性人,读经、念佛,长学精进;六时行道,长坐不卧;广学多闻,以为佛法;此等众生,尽是谤佛法人。
前佛后佛,只言见性。诸行无常,若不见性,妄言:“我得阿耨菩提”此是大罪人。十大弟子,阿难多闻中得第一,于佛无识,只学多闻,二乘外道皆无识佛,识数修证,堕在因果中。是众生业报,不免生死,远背佛意,即是谤佛众生,杀却无罪过。经云:“阐提人不生信心,杀却无罪过。”若有信心,此人是佛位人。若不见性,即不用取次谤他良善,自赚无益。善恶历然,因果分明。天堂地狱,只在眼前,愚人不信,现堕黑暗地狱中;亦不觉不知,只缘业重故,所以不信。譬如无目人,不信道有光明,纵向伊说亦不信,只缘盲故,凭何辨得日光?愚人亦复如是。现今堕畜生杂类,诞在贫穷下贱,求生不得,求死不得。虽受是苦,直问著,亦言:“我今快乐,不异天堂。”故知一切众生,生处为乐,亦不觉不知。如斯恶人,只缘业障重故,所以不能发信心者,不自由他也。若见自心是佛,不在剃除须发,白衣亦是佛。若不见性,剃除须发,亦是外道。
问曰:“白衣有妻子,淫欲不除,凭何得成佛?”答曰:“只言见性,不言淫欲。只为不见性;但得见性,淫欲本来空寂,不假断除,亦不乐著,纵有余习,不能为害。何以故?性本清净故。虽处在五蕴色身中,其性本来清净,染污不得。法身本来无受,无饥无渴,无寒热,无病,无恩爱,无眷属,无苦乐,无好恶,无短长,无强弱,本来无有一物可得;只缘执有此色身,因即有饥渴、寒热、瘴病等相,若不执,即一任作为。若于生死中得大自在,转一切法,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,无处不安。若心有疑,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。不作最好,作了不免轮回生死。若见性,旃陀罗亦得成佛。”
问曰:“旃陀罗杀生作业,如何得成佛?”答曰:“只言见性,不言作业。纵作业不同,一切业拘他不得。从无始旷大劫来,只为不见性,堕地狱中,所以作业,轮回生死。从悟得本性,终不作业。若不见性,念佛免报不得,非论杀生命。若见性,疑心顿除,杀生命亦不奈他何。”
自西天二十七祖,只是递传心印。吾今来此土,唯传顿教大乘,即心是佛,不言戒、施、精进、苦行;乃至入水火,登剑轮,一食卯斋,长坐不卧,尽是外道有为法。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,即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言传心,更无别法。若识此法,凡夫一字不识亦是佛。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,假使身破如微尘,觅佛终不得也。
佛者亦名法身,亦名本心,此心无形相,无因果,无筋骨,犹如虚空,取不得。不同质碍,不同外道。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,其余众生迷,人不明了。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,若离此心,即无能运动;是身无知,如草木瓦砾。身是无情,因何运动?若自心动,乃至语言、施为运动,见闻觉知,皆是心动。心动用动,动即其用。动外无心,心外无动。动不是心,心不是动。动本无心,心本无动。动不离心,心不离动。动无心离,心无动离,动是心用,用是心动。动即心用,用即心动。不动不用。用体本空,空本无动,动用同心,心本无动。故经云:“动而无所动,终日去来而未曾去,终日见而未曾见,终日笑而未曾笑,终日闻而未曾闻,终日知而未曾知,终日喜而未曾喜,终日行而未曾行,终日住而未曾住。”故经云:“言语道断,心行处灭;见闻觉知,本自圆寂。”乃至嗔喜痛痒何异木人,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。故经云:“恶业即得苦报,善业即有善报,不但嗔堕地狱,喜即生天。”若知嗔喜性空,但不执,即诸业脱。若不见性,讲经决无凭,说亦无尽。略标邪正如是,不及一二也。
颂曰:
心心心,难可寻,宽时遍法界,窄也不容针。
我本求心不求佛,了知三界空无物;
若欲求佛但求心,只这心心心是佛。
我本求心心自持,求心不得待心知;
佛性不从心外得,心生便是罪生时。
偈曰:
吾本来此土 传法救迷情
一华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
《达摩大师血脉论》终

回向偈
文殊师利勇猛智, 普贤慧行亦复然。
我今回向诸善根, 随彼一切常修学。
三世诸佛所称叹, 如是最胜诸大愿。
我今回向诸善根, 为得普贤殊胜行!